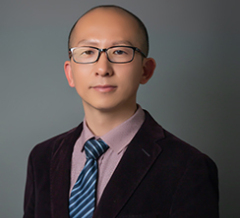中国的现代化作为由欧洲文明肇其端的全球转型的组成部分,是对西方现代性挑战的回应。在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的晚清危机语境中,中国转型之“古今”问题始终与“中西”问题相纠缠。因而,“中西古今”成为中国启蒙运动的一个特定的核心命题,这也是中国之外源型现代化的一大思想表征。

严复的中西融合论立基于社会进化论,从现代文明的视角,以富强为其旨,主张大力摄取西方现代文明,改革中国文化中的旧宗法传统,实现中西新旧的融合会通。严复之中西融合论既超越了洋务派之保守的中体西用论,又未落入五四新文化人激进的全盘西化论,体现了晚清启蒙思想之温和稳健的英伦色彩。
中体西用论批判
甲午丧师,举国震惊。1895年春,在民族危亡的悲情时刻,严复于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雄文,开晚清启蒙运动之先河。严复超越洋务派的远见卓识在于:一国的海军不是孤立的军事力量,而是其整个文明系统的组成部分。故富强不仅在坚船利炮,而在社会的文明进步。这种从文明系统看海军的宏阔视野,使海军教官严复放眼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成为晚清第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
在《原强》中,严复阐释达尔文进化论,倡言“生存竞争”之天演公理;借鉴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论,主张以“陶铸国民”为中国富强之道。严复从斯宾塞学说得到启发,国家是一个生物般的有机体,国民犹如细胞。积民而成国,民强则国强,民弱则国弱。国民素质的优劣由于民力、民智、民德的高下,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民的竞争。严复指出,战败不足以悲,可悲的是民智已下,民德已衰,民力已困。因而,中国问题的要害在于国民。洋务运动振兵兴业之所以难收成效,在于其治标不治本。其本在民智、民力、民德的提升。
1902年,严复在致《外交报》主人信中批判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中西主辅论和政本艺末论,并阐述了其中西融合的文化主张。关于中体西用论,严复批驳了其体用割裂的文化折中论:“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
在严复看来,以中学为主而辅以西学的中西主辅说,其谬误与中体西用论同。“一国之政教学术,其如具官之物体欤?有其元首脊腹,而后有其六府四支;有其质干根荄,而后有其支叶华实。使所取以辅者与所主者绝不同物,将无异取骥之四蹏,以附牛之项领,从而责千里焉,固不可得,而田陇之功,又以废也。晚近世言变法者,大抵不揣其本,而欲支节为之,及其无功,辄自诧怪。”
在《主客平议》(1902年)中,严复进一步指出了张之洞政本艺末说之推重西政而又拒斥民主的自相矛盾之处:“往者某尚书最畏民权自由之说,亲著论以辟之矣,顾汲汲然劝治西学,且曰西艺末耳,西政本也,不悟己所绝重者,即其最畏之说之所存,此真可为强作解事者殷鉴矣。”
严复认为,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体与用具有共生性而不可分割。中西文化各有其体与用,二者决不可随意分割和拼接。洋务派迎“西用”之技术经济而拒“西体”之政治伦理的有限改革,舍本逐末,其失之于二元拼接的文化观。
拥抱现代文明
17世纪以来,现代文明伴随着英国“光荣革命”、工业革命而崛起于英伦三岛,继而波及欧陆,欧洲文明经历了一场从前工业世界到工业化时代的“大转型”(卡尔·波兰尼语)。这一席卷世界的现代化“大转型”,是一场改变人类命运的“全球转型”。英国国际政治学家巴瑞·布赞(Barry Buzan)和乔治·罗森(George Lowson)在《全球转型——历史、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的形成》(2015年)中指出,发轫于欧洲而后波及世界各地的现代性发展,以工业化、理性的国家建构和进步论意识形态为主要推动力,在19世纪掀起波澜壮阔的全球转型,从而奠定和造就了发展至今的我们所处的现代世界。
严复是现代文明的“盗火者”。这位曾留学英伦的海军教官,是晚清第一个认识西方现代文明之意义的启蒙思想家。甲午兵败国辱,严复痛切地认识到“世变之亟”,“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虽然甲午之役兵败东邻日本,但严复则将目光投向西方,将世变危亡之因归为西方文明的东渐。对西方富强原因的追寻,使他发现了西方“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现代文明。
严复以“西学圣人”著称,其以“译书不朽”自勉的西书翻译事业,其精心选择的西学经典极具深意,可谓对全球转型之工业化、理性的国家建构和进步论意识形态三大挑战的全面回应。如亚当·斯密探究工业化社会市场经济原理的《原富》(今译《国富论》),孟德斯鸠研究宪政民主政体的《法意》(今译《论法的精神》),赫胥黎推阐进化论的《天演论》(今译《进化论与伦理学》),以及密尔论自由的经典《群己权界论》(今译《论自由》)等。从这些西籍的选择,足见严复洞察西方现代文明之底蕴的慧眼独具。
严复发现,近代欧洲发生了空前的历史巨变。这场深刻变革是全方位的,它广涵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领域。严复强调,西方的富强,是自由民主的民族国家的产物。“今夫国者非他,合亿兆之民以为之也。国何以富?合亿兆之财以为之也。国何以强?合亿兆之力以为之也。”“乃今之世既大通矣,处大通并立之世,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者;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
严复以甑克思“蛮夷社会——宗法社会——国家社会”三阶段论考察社会进化,以国家为文明之基本表征。严复强调,“文明社会”与“初级社会”的根本差异,在于是否脱离宗法社会:“初级社会,大抵不离家族形质,而文明社会不然。”文明,含进步之义,即由宗法而国家的进化。
严复认识到,欧洲工商社会代表了现代文明进化之趋势。他以文明与野蛮、开化与未化为文化评判的标准。严复指出,在全球大通的现代世界,开放是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近世三百余年,舟车日通,且通之弥宏,其民弥富;通之弥早,其国弥强。非彼之能为通也,实彼之不能为不通也。通则向者之礼俗宗教,凡起于一方,而非天下之公理,非人性所大同者,皆岌岌乎有不终日之势矣。……而非天下之公理,非人性所大同,其终去而不留者。”以亚欧杂处的俄罗斯为例,其受诸近代欧洲文明之形下之器,又守诸亚洲之专制政治,但终以自败,而酿成革命之局。严复的深刻独到之处,在其对“文明”与“文化”所持的不同方针:“文明”是人类的、普世的,其与“野蛮”相对立,代表“天下之公理”和“人性所大同”;“文化”则是民族的、特殊的,其为“起于一方”的传统礼俗宗教。在世界交通之时代,现代“文明”必然与传统“文化”形成冲突。而那些地方性的传统礼俗宗教,其非天下之公理和非人性所大同的元素则必将趋于消亡。质言之,“文明”表征“天下之公理”和“人性所大同”,反之则为“野蛮”。而对“文化”之存弃,则以是否合乎“文明”为标准。对于中西新旧问题,严复主张拥抱“文明”,对“文化”去伪存真。
严复以“文明富强”为中国救亡图存的必由之路,对西方文明主张开放,而反对排拒文明的守旧。对他来说,“文明富强”不可分割,文明是富强之因,富强是文明之果。西方富强的本源,是其“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现代文明制度。他认为,追求富强唯有拥抱文明,排外而拒斥文明,则于救亡徒劳无益。严复的结论是:“期于文明可,期于排外不可。期于文明,则不排外而自排;期于排外,将外不可排,而反自塞文明之路。”
守旧派忧虑亡国灭种、孔教失坠而求“保种保国保教”,固守“夷夏之防”以抗拒西方文明。严复则坚持认为,开放是现代世界之大势所趋,守旧必不可行,只能加速灭亡。“可知外物之来,深闭固拒,必非良法,要当强力不反,出与力争,庶几磨厉玉成,有以自立。至于自立,则彼之来皆为吾利,吾何畏哉?”
中西文化之比较
在《论世变之亟》中,严复突破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模式,追寻致欧美于富强的西方文明之精华。在他看来,洋务运动仿行西方之船坚炮利、声光化电、工业商务等,皆为舍本逐末,而并没有把握西方文明的精髓。西方文明的两大命脉,是黜伪而崇真之学术和屈私以为公之法政,即科学与民主。而自由与不自由,则是科学与民主在西方和中国成败的关键。
在严复之前,张树声、郑观应等晚期洋务派亦对“西体”之议会制度有所认识,并主张对西方宜体用兼采。而严复留英时的师友、驻英公使郭嵩焘则对英伦议会政治尤有深见。但是严复对西方“自由为体”的认识,则石破天惊,慧眼独具。
严复以“自由”一语,把握了中西文化问题的枢纽。自由是现代性的价值核心,自由主义是西方现代社会的基本哲学和秩序原理,而中国文化则向来匮缺自由传统。严复指出:“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勿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中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然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相同则大不可也。何则?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
在严复看来,自由与不自由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中西文化的一系列差异由此而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于财用,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接物,中国重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为学,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
严复进而揭示了中西历史观之循环论与进步论的歧异。“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中国圣人“故宁以止足为教,使各安于朴鄙颛蒙,耕凿焉以事其长上,是故春秋大一统。一统者,平争之大局也”。这种好古与力今、治乱循环与日进无疆之对立的历史观,表征着农业社会之循环论史观与工业社会之进步论史观的深刻分歧。
在《原强》中,严复指出,西洋“无法”(风尚)与“法”(制度)并用而皆有以胜我国之处。其自由平等,是无法之胜。其官工商贾章程明备,则是有法胜。其民不仅高大鸷悍而胜我,而且德慧术知亦为吾民所必不及。故凡经济法律军事交通,凡所以保民养民之事,其精密广远远胜中国。且其为事又一一皆本之科学。“推求其故,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严复这一“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西方文明论,直抵现代西方文明之堂奥,其不仅超越了晚清洋务派和维新派的认识,即后起的五四新文化派亦无出其右。
关于西方富强的原因,严复将其归结为自由自治的国民:“是故富强者,不外利民之政也,而必自民之能自利始;能自利自能自由始;能自由自能自治始,能自治者,必其能恕、能用絜矩之道者也。”自治、自由、自利的国民,是国家富强的基础。而这正是中国人所匮缺的。
比较中西政治之异同,使严复认识到,东西立国相异,而国民资格亦由是而大不同。西方君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君师相兼。且中国社会为宗法社会,故帝王又称为民父母。西方君主专为君,故所重在兵刑,而礼乐、宗教、工商、教育皆可放任民众以自为之。中国帝王下至宰守,皆以其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君上之责任无穷,而民众之能力则无由以发达。若君仁,则视其民犹儿子,若君暴,则视其民犹奴隶。为子为奴,于其国无尺寸治权和丝毫法定之权利。从中西政教之异,可寻西方富强的根本。
在严复看来,中西伦理的重大差异源于基督教与儒教。“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自由,故贵信果。东之教立纲,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亲。尊亲,故薄信果。然其流弊之极,至于怀诈相欺,上下相遁,则忠孝之所存,转不若贵信果者之多也。且彼西洋所以能使其民皆若有深私至爱于其国与主,而赴公战如私仇者,则亦有道矣。法令始于下院,是民各奉其所自主之约,而非率上之制也;宰相以下,皆由一国所推择。是官者,民之所设以厘百工,而非徒以尊奉仰戴者也,抚我虐我,皆非所论者矣。”
关于中西政治,严复根据孟德斯鸠之分权学说,分析了西方民主宪政与东方专制政治之优劣。“欲观政理程度之高下,视其中分工之繁简。今泰西文明之国,其治柄概分三权:曰刑法,曰议制,曰行政。……此文明通法,而盎格鲁之民尤著。故其国无冤民,而民之自任亦重。泰东诸国,不独国主君上之权力无限也,乃至寻常一守宰,于其所治,实皆兼三权而领之。故官之与民,常无所论其曲直。”因而中西政治的差异是根本性的。治体之顺逆良楛是因,而国势之强弱和民生之贫富是果。严复进而认识到,皇权专制造成了中国国民的奴隶性。比较西洋民主政治与中国专制制度对国民品性的影响,严复指出,西洋以国家为人民之公产,王侯将相为国家之公仆。中国则尊君抑民,以臣民为奴隶。
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严复认为,华风之敝“始于作伪,终于无耻”,是因“其教化学术非也。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祸首,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嬴、李以小人而陵轹苍生,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后世其用意虽有公私之分,而崇尚我法,劫持天下,使天下必从己而无或敢为异同者则均也。因其劫持,遂生作伪;以其作伪,而是非淆、廉耻丧,天下之敝乃至不可复振也。此其受病至深,决非一二补偏救弊之为,如讲武、理财所能有济。盖亦反其本而图其渐而已矣!否则,智卑德漓,奸缘政兴,虽日举百废无益也”。
对于守旧派之“保教”说,严复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中国虽奉孔教为国教已两千年,但民间信奉的实为佛教和土教。穷乡僻壤不乏佛寺尼庵,民间习俗亦多与佛教有关。盛行于民间的土教,以多鬼神和不平等为特征。而孔教在民间则影响有限。孔教之高处,在于不设鬼神,不谈格致,专明人事,平实易行。但中国民智未开,与孔教不合。孔教虽被奉为国教,而百姓实未归孔教。于是适值佛教东来,其多鬼神之说与未开化之人脑气最合,而渐成风俗。中国今日实未尝行孔教,故不存在“保教”问题。
严复的中西文化观建基于进化论,根据甑克思的社会进化理论,人类社会经历了“图腾——宗法——国家”的进化阶段。现代西方已进入国家社会,而中国则仍处于古老的宗法社会。中西文明的对立冲突,即源于古代宗法社会与现代国家社会的差异。因而中西之别,归根结底是古今之争。处于“世变之亟”的中国,“世变”者,“古今之变”也。“中国之不兴,宗法之旧为之梗也。”“使中国必出以与天下争衡,将必脱其宗法之故而后可。”严复中西文化观的深刻高明,不仅在于其揭示了西方现代文明“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精髓,而且在于其具有由宗法而国家“大转型”之“古今之变”的历史进化视野。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之融合
晚清中国处于古今之变的大转型时代。严复对现代西方文明抱开放的心灵,对中国传统持去芜存精的辩证态度。他所追求的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的融合。他主张:“然则今之教育,将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欤?曰:是又不然。……不知是乃经百世圣哲所创垂,累朝变动所淘汰,设其去之,则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独别择之功,非暧姝囿习者之所能任耳。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其为事之难如此。”严复“统新故,苞中外”的文化方针,旨在中西新旧的会通融合。其对传统的温和保守态度,近于从亚当·斯密到约翰·密尔和斯宾塞之英伦自由主义“于保守中求进步”的调和风格。
严复对中西文化的取舍,以富强为宗旨。他主张,今日中国最大的病患是愚、贫、弱,故凡可以愈愚、疗贫、起弱之事皆可为。而三者之中尤以愈愚为最急,因为正是愚昧使中国日由贫弱之道而不自知。
对于中西文化,严复主张中国急需大力输入西方文化以补本国文化之短缺。作为晚清“西学圣人”,严复以输入西学为业,翻译了《原富》等一系列欧洲社会科学经典著作。对于中国传统,有废弃传统的破坏者之说和护存国粹的保守者之说,二者异曲同工,其内心认为中国旧学之将废则同。严复则认为,“破坏保守,皆忧其所不必忧者也。果为国粹,固将长存。西学不兴,其为存也隐;西学大兴,其为存也章。盖中学之真之发现,与西学之新之输入,有比例为消长者焉。不佞斯言,所以俟百世而不惑也”。严复这一自信为永恒真理的观点,确为中西文化观之极富辩证性的深刻洞见。中学之真之发现与西学之新之输入,相反相成。中学之真之发现,有赖于西学之新之输入,新西学愈输入,中学之真愈发现。
文化认同:从寻求富强到护存国性
在由西方波及世界的全球转型过程中,现代文明的发现与本土文化的自觉,是非欧民族两个反向的辩证思想过程,西化主义与保守主义表征着文明与文化的张力。犹如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所谓经济社会“大转型”,市场经济的扩张伴随着社会保护运动的反抗。
晚清以降,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追求“民主与科学”,表征着一个世界现代文明发现的过程。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中所谓国人认识西方由“学术之觉悟”而“政治之觉悟”而“伦理之觉悟”的递进,即一个文明发现的过程。另一方面,清末民初,思想界又有一股护存本土文化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如刘师培、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倡言“国粹”“国魂”“国性”的思潮,它表征着一个全球转型中华夏古国回应西潮、寻求文化主体性之文化自觉的过程。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表征着西学东渐神州之深刻的文明冲突。
辛亥革命后,儒家文化随帝制崩解而解纽,中国陷入空前深刻的秩序危机和意义危机。晚清维新派诸巨子纷纷转而护持文化认同,康有为鼓吹“国魂”并发动孔教运动,梁启超1912年发表《国性论》而倡言中华特性,严复1913年发表《思古谈》、《读经当积极提倡》,阐扬“国性”。民初这股护存国性的文化认同思潮,1918年以梁济殉道自沉而震惊世人,梁氏在遗书《敬告世人书》中沉痛警告:国性不存,国将不国。
民国初年,晚年严复的思想关切,已从追寻富强的文明变革转为护存中华特性的文化认同,他对西潮冲击下中国文化的命运忧心忡忡,而力倡保存“国性”。他在《思古谈》中写道:“诸公所以醉心于他族者,约而言之,什八九皆其物质文明已耳。不知畴国种之阶级,要必以国性民质为之先,而形而下者非所重也。中国之国性民质,根源盛大,岂可厚诬。……如斯宾塞所谓动、平、冲者,而成不骞不崩之国种,而其所以致然之故,必非乞灵他种之文明余唾而后然也。其国性民质所受成于先圣先王数千年之陶熔渐渍者,有以为之基也。”
同年,严复在中央教育会演说《读经当积极提倡》中指出:“大凡一国存立,必以其国性为之基。国性国各不同,而皆成于特别之教化,往往经数千年之渐摩浸渍,而后大著。”只要国性长存,则虽被外族制服,其国其天下尚非真亡,如宋之入元,明之为清,虽改朝换代,但其伦理法制基本如前,而入主之族则无异归化。而墨西哥、希腊、罗马、印度、埃及,古国文化湮灭,国虽未易主,实已真亡。国性不存,古国灭亡。严复强调:“我辈生为中国人民,不可荒经蔑古。”在严复看来,辛亥革命,亦以《易传》汤武“顺天应人”、《礼运》“大同”、《孟子》“民贵君轻”诸大义为依据,而后有民国之发现。儒经中更有永恒的为人之准则,如君子喻义,小人喻利,欲立立人,欲达达人,见义勇为,恕道,孟子言性善、严义利,皆为做人最宝贵的伦理原则。人之所以为人,国之所以为国,天下之所以为天下,则舍求群经之中莫有合者。即使西方人之成俗为国,其处事亦必与儒家经法暗合,方可利行久大,可见经之道大而精。读经关乎国性之存亡。
在严复看来,在社会进化中,传统既有其变,亦有其不变。现代社会政治虽变,而伦理则不变。此亦为其甲午后上清帝书中的观点。严复强调,今日所谓人伦与从前并无不同,所变的不过是所谓“君”,以抽象之全国易具体之一家。
1914年,时任约法会议议员的严复提出《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议案,阐扬“忠孝节义”。他强调:“国于天地,其长存不倾,日跻强盛者,必以其民俗、国性、世道、人心为之要素。其所由来旧矣。……独至国性丧亡,民习险诈,则虽有百千亿兆之众,亦长为相攻相惑不相得之群,乃必鱼烂土崩而不可救耳!”严复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国民是其单位,道德则是其相吸力的大功能,因而必凝聚道德为国性,才能使国基坚实。严复倡议以“忠孝节义”为中华民国之立国精神:“吾国处今,以建立民彝为最亟,诚宜视忠孝节义四者为中华民族之特性。而即以此为立国之精神,导扬渐渍,务使深入人心,常成习惯。”
民国初年,晚年严复的中西观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其思想关切已从“文明”转向“文化”,从拥抱西方现代文明转而保守中国传统文化,从追求富强转而护存国性。对于儒家文化,则从倡言“变革”而转向保守“认同”。其“国性”论,置重中国之文化认同、文化特性,将“国性”之存亡视为中国之兴衰的关键。
结语
在危亡之秋的晚清社会,严复之“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西方文明论、生存竞争的天演论、“开民智”的启蒙思想以及中西融合的文化观,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犹如一道闪电划破甲午后危亡悲情弥漫的神州夜空。
严复慧眼独具,其“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西方文明论,直抵西方现代文明之堂奥,揭示了现代社会的价值内核和秩序原理。他以自由为中西文明之分水岭、以宗法社会与国家社会区分中西所处文明阶段的观点,以其全球历史进化的现代视野,揭示了中国问题的本质,其文明观代表了晚清进步思想界对西方文明最深刻的认识。严复的西方观不仅超越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而且优于康有为的立宪主义,康氏拒斥自由民主的君宪论并未摄取英国自由主义的精髓。在晚清以降国人认识西方现代文明的过程中,“西学圣人”严复的西方论之于现代“文明”的发现居功至伟。
严复“统新故,苞中外”的中西融合论,深受英国思想家斯密、密尔、斯宾塞和莫列等人思想之影响,而颇具英伦保守的自由主义之调和色彩。严复这种温和稳健的调和论,与梁启超的文化调和论相近,形成了清末启蒙思潮的英伦风格。它既超越了洋务派之保守的中体西用论,又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带有法国色彩的激进反传统主义大异其趣。
严复洞察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意义,其所谓“文明”与“野蛮”相对,表征人类社会进化的进步性,而西方正是工业化时代现代文明的代表。严复尤为深刻之处,在于其普遍“文明”与特殊“文化”的区分,他以人类进化之工业社会的视角理解西方文明,并以天下之公理和人性所大同为文化评判取舍的标准。由此,他揭示了全球转型时代中西问题的本质:中国现代化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的融合。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摄取西方现代文明之“变革”与护持中国文化之“认同”的辩证过程,其目标为泱泱古老中华之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之“旧邦新命”的浴火重生。晚清以降,危机中的中国之“保国”“保种”与“保教”的两难困境在于:不变法变教,则不能保种保国。此即中国文化转型之变革与认同的深刻吊诡。晚年严复关于“国性”问题的思考,凸显了全球转型时代之中国文化认同的意义,是其中西融合思想的深化。民国初年,受欧洲大战和民国秩序危机的双重刺激,严复告别西方文明而复归中国传统。从晚清倡言“西学”到民初保存“国性”,严复一生徘徊于现代“文明”与中国“文化”之间的思想困境,凸显了中国文化现代化之“变革”与“认同”两大主题的深刻张力。